我的从医路—回望初心谈感想|雷海芳:以齿为尺,丈量初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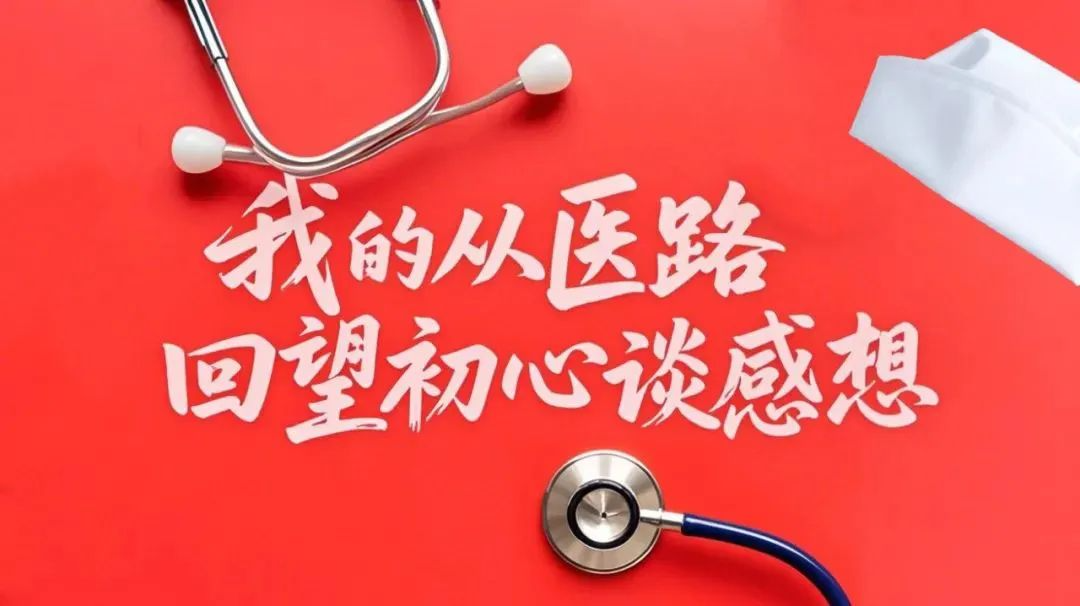
叩启医门,始于热爱
2007年第一次见到口腔修复诊室的光影:牙椅灯在患者口中投下温柔的光斑,医生指尖的器械与口腔亲密接触,像在进行一场精密的微雕。那时我便知道,这方不足两平米的诊疗台,将是我一生的“战场”。从院校实验室里反复练习取模灌模,到临床跟诊时为老人戴上第一副义齿后,她颤抖着说出“能咬苹果了”,这份职业的温度,早已在无数次磨改蜡型、调整咬合中,渗进了指缝。

修的是牙,暖的是人
曾遇过一位因外伤缺牙的年轻人,复诊时总戴着口罩沉默。我特意在修复方案里设计了仿真牙龈形态,当他对着镜子反复摩挲新牙,忽然抬头说“终于敢笑了”——那一刻我懂得,我们修补的不仅是牙齿,更是被生活啃噬过的自信。这些年,为各类患者做各种类型的义齿,每一次俯身操作时,额头的汗水都在提醒:医者手中的器械,承载着患者对“好好吃饭、体面生活”的最朴素期待。

以技修身,以心传灯
如今带教时,我总把“三毫米原则”挂在嘴边:嵌体边缘误差不能超过三毫米,这是技术的底线,更是对患者的良心。这些年,从传统石膏模型到数字化口扫,从金属冠到全瓷修复体,技术在变,但“有时,去治愈;常常,去帮助;总是,去安慰”的信念没有变。每当看到年轻医生为调磨半度咬合反复比对,看到患者攥着复诊记录像握着生命线,便愈发确信:在这个追求“效率”的时代,我们守护的,恰恰是时光淬炼出的匠心——那是对每个牙尖斜面的苛求,对每次医患对视的真诚,更是穿破口罩阻隔,用眼神传递的“别怕,有我在”。
齿间藏山河,医者知春秋。愿此生如牙体预备般,磨去浮躁,留下对生命的敬畏与温柔。
供稿:铜仁市人民医院口腔科 主治医师 雷海芳

